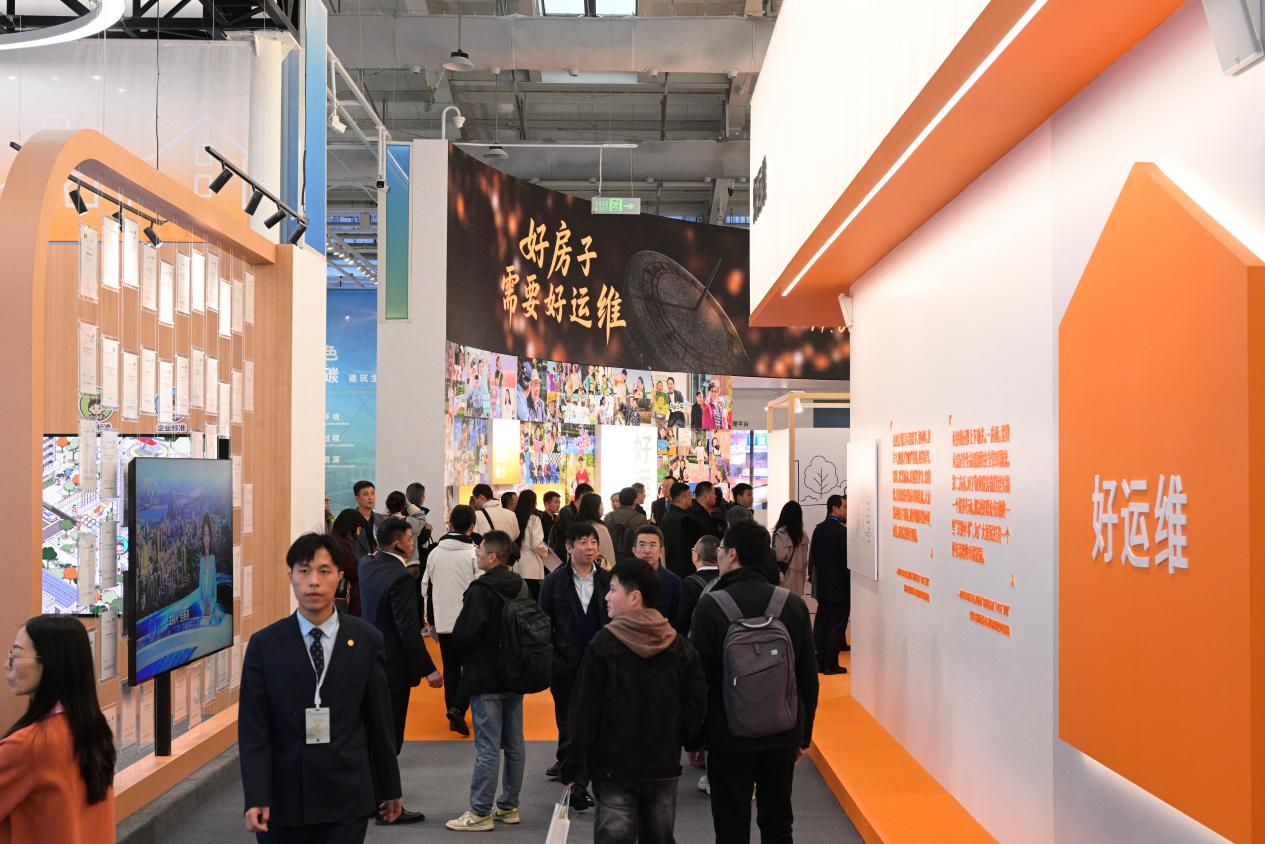从投下反对票到公开质疑程序合规性,大股东平安系与华夏幸福之间的矛盾已摊上台面。
继平安系董事王葳登报声明“完全不知情”后,11月24日,华夏幸福董事兼副总裁冯念一公开表态称,当前正值公司预重整的关键阶段,各方应立足事实,以整体大局为重。在他看来,预重整是华夏幸福实现债务风险出清、摆脱困境的重要契机,也将有助于维护广大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的权益。
这场围绕预重整程序是否合规的博弈,表面是治理规则的分歧,实则是利益角力与化债路径的深层分歧。
双方公开“喊话”
矛盾的爆发始于11月17日华夏幸福披露的两则公告。
其一显示,债权人龙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华夏幸福未能按期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廊坊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同步启动预重整程序,而法院已正式受理该预重整申请,华夏幸福方面则标注“对此无异议”。
公开信息显示,龙成建设曾为华夏幸福承接市政工程施工总包业务,经竣工验收、结算付款后,华夏幸福仍欠付该公司工程款约417.16万元。
另一则公告明确,廊坊中院已依法指定华夏幸福司法重整清算组,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
出乎意料的是,华夏幸福平安系董事王葳通过登报方式发表声明,直接戳破“公司无异议”的表面共识:“本人对该公告的发布事宜完全不知情,公司未在公告发布前通过任何形式告知本人,未向本人提供相关文件资料,更未就此事项征求本人意见或召开董事会会议进行审议。该公告的发布完全绕过本人,严重违反了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公司治理的基本程序。”
面对王葳的公开质疑,冯念一的回应则聚焦于预重整的整体价值,强调各方需兼顾全局利益。其表示,现在正值公司预重整的关键时期,各方应实事求是,从全局利益出发考虑问题。预重整是华夏幸福彻底化解债务风险、实现脱困发展的一次难得机会,有利于保护广大债权人及中小股东权益。
与此同时,11月21日华夏幸福债委会发起的一项议案——《授权主席单位平安资管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华夏幸福进行专项财务尽调的议案》,并获得通过。
根据决议,华夏幸福债委会将授权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债委会名义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聘请一家有专业能力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华夏幸福的财务状况开展专项尽职调查工作。此次财务尽调主要针对化债方案不透明、资金去向存疑等问题。债委会工作组将自2025年11月24日起进驻华夏幸福,开展专项财务尽调的前期准备工作。
对此,华夏幸福方面回应称,正在依法积极配合临时管理人开展包括资产负债调查在内的各项工作以确保预重整程序顺利推进,公司无法定义务配合金融债委会另行对公司开展财务尽调。
程序是否合规?
王葳为平安系派驻华夏幸福的董事代表,此次“撕破脸”,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平安的立场。这场争议似乎早已超越单个董事的权限之争,演变为两大主体在债务重整路径上的深层博弈。
从王葳的声明来看,其质疑的核心焦点清晰指向程序合规性:这次的预重整是否必须经过董事会审议?
冯念一向媒体指出,上市公司预重整有两种申请模式,一种是被债权人申请预重整,一种是上市公司主动申请预重整。被债权人申请的预重整不需要开董事会、股东会;只有上市公司主动申请的预重整,才需要提交董事会、股东会审议,这是上交所自律监管13号指引第9条明确规定的。
记者查阅相关条款发现,第9条规定确实对上市公司主动申请重整作出刚性要求:上市公司拟主动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的,应当充分评估是否符合《企业破产法》等规定的条件、被法院受理的可行性以及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等,并提交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但针对债权人发起的情形,仅要求公司如对申请有异议应及时披露,未明确设置董事会审议环节。
冯念一方据此认为,债权人申请的预重整不属于董事会审议范围。
对此,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玉臣律师分析称,从目前情况来看,华夏幸福预重整争议的核心可能是预重整程序合规性存疑、利益主体信息不对称,以及权限边界冲突的问题。
王玉臣进一步解释道,这集中反映出三大问题,一是我国预重整制度立法缺失导致的实践“无法可依”困境。这些年随着资不抵债企业大幅度增加,一些地方开始尝试“预重整”,但破产法中其实对预重整是没有明确规定的。二是企业内部治理(比如董事会决策)与程序衔接不畅,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预重整或重整都需要经过企业同意。三是债权人对化债透明度的迫切需求与信息供给不足的矛盾,这一点在很多案件中也显得尤为突出。
八年联姻从甜蜜到破裂
事实上,两者之间的矛盾浮出水面,并非没有征兆。
王葳此前曾对华夏幸福的关键议案投出反对票,诸如2025年半年报及一项资产减值方案,理由直指“置换贷处理不审慎”。
所谓“置换贷方案”,始于2024年10月。根据该安排,华夏幸福拟以2元价格,向廊坊市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旗下廊坊泰信、廊坊安尚两家子公司全部股权,用以置换其对廊坊银行约225.75亿元的债务。
尽管该方案于2025年5月末获股东会通过,显然平安系显然对这一资产处置存疑。
时光倒回八年前,平安与华夏幸福甜蜜“牵手”。2018年7月,华夏幸福与中国平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平安资管以每股23.655元的价格受让华夏幸福19.70%股权,对价137.7亿元。次年1月,平安再度增持5.69%,持股比例升至25.25%,成为重要战略股东。
然而好景不长。2021年2月,华夏幸福公开违约,债务危机爆发。同年9月,因原控股股东华夏控股所持股份被强制处置,平安被动成为第一大股东,但未寻求实际控制权,公司仍由王文学方面主导经营。这种治理机制,也为后来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随着多笔债务逾期,华夏幸福业绩一路下行。
当年牵手时,华夏幸福签订了对赌协议,约定2018年至2020年净利润增长率需分别不低于30%、65%、105%。但2020年起公司利润大幅下滑,此后更是多年亏损。华夏幸福股价更是一落千丈,从平安入场时的20多元跌至目前2元出头,市值大幅蒸发。
平安也因此承受巨额拖累。2021年初,平安相关负责人曾透露,平安对华夏幸福整体风险敞口达540亿元。当年,平安对华夏幸福相关投资资产进行减值计提、估值调整及权益法损益调整金额合计为432亿元。
2025年8月,平安资管公告拟减持不超过3%的股份,被市场视为逐步退出信号。
重整之路何去何从?
表面是程序争议,实质或许是利益冲突。
在上海镜鉴智合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宏伟看来,平安与华夏幸福当前的矛盾不过是一根导火索。根本原因在于,在华夏幸福的债务重整过程中,平安或许深感自身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一旦认为潜在损失将远超预期,长期积压的矛盾便难以掩盖。
同时,张宏伟也指出,这也折射出股东权责的失衡。平安作为第一大股东,有投资权,但经营权和决策权不对等。在市场上行时,各方尚可相安无事;一旦企业“爆雷”、进入重整,这种不对等的治理结构便成为矛盾爆发的土壤。
即便没有平安系的反对,参照此前金科股份的案例,华夏幸福的重整之路也注定不会平坦。这将是涉及各类债权人、中小股东等多元利益的又一场艰难博弈。
封面图/豆包大模型制图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段文平
编辑 杨娟娟
校对 陈荻雁